
我的老家是沂蒙山区留田村,是罗荣桓元帅面对十倍日军包围,不费一枪一弹神奇突围的地方。癸卯年我回故乡七八次,多得自己都记不清,而往年只回去一两趟。回去的时候少,过去的场景仍历历在目。

年关,四五岁的儿子不愿跟着串门,而是顶着寒风到河边游玩,恰巧一群鸭子从桥墩旁的溪流游向桥底,我和孩子不约而同地唱起“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,快来快来数一数,二四六七八……”

儿子八九岁时,我们爬三角山去野炊,待到山腰,早有人席地就餐,旁边控山水汩汩涌流,洗把脸凉气逼人,驱走淋漓大汗,取出随身携带的面包、火腿和饮料,一会儿风卷残云吃尽,待及鼓足勇气登顶,但见汶河如玉带蜿蜒缠绕,沂新线上车辆如甲壳虫般缓慢爬行,山下湖泊如镜面镶嵌在山脚。

有次计划去临沂的水上公园玩,到达后才发现所有沿河娱乐设施,因疏通河道存隐患被拆,最后回到故乡,带小女儿在河滩玩沙漏、捡鹅卵石,在河里拾贝壳、捞小鱼,玩的不亦乐乎。
故乡,许多次出现在梦境。有我的启蒙小学,好多次梦中背着书包回到母校,后来才发现老学堂拆得片瓦无存,做梦是因为残存着记忆吗?有奶奶的老家,好多次梦中又回到老屋,明知她已去世仍忍不住进去,有时她竟然真的端坐在屋中。

故乡,许多次地出现在我的笔端。《上山捉鱼》描写苇塘的鱼儿在雨后会溯流而上,人们竞相上山,在山间溪流捉鱼的奇妙场景;《汶河畅想》描写洪水来临漫过桥面一人多深,冲刷河岸一次次垮塌,人们焦虑地在河岸观看,拴在对岸的黄牛自己凫水回来,主人担忧的母鹅带领四只小鹅艰难游回,最小的那只竟然被围护中央,还有愣小子跳入洪水中,在大家惊诧的目光中打捞回冲下的木头。

故乡,更多地变化映入我的眼帘。去年间,村庄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。留田突围纪念馆已竣工,从亲友发给我的蓝图变成现实,让光荣的红色历史得以更好传承,旁边新建村庄党群服务中心,前边安装各类健身器械。村西北的红心湖,承载了许多儿时的记忆,冬天厚厚的冰层上,即使人们在上面蹦跳,也只能听见从远处传来的“咔咔”声,以前的汪塘变成湿地公园,修建的环湖栈道、休闲公园,几次开车惊鸿一瞥,尚未细细浏览。

故乡,不仅有生我养我的父母,更有滋养我不断成长的沃土。留田,这片躺在汶河弯的厚土,用亿万年冲积的平原,满足多少代人的温饱,萦绕着无数人的牵挂。如今,它正变得更加富饶美丽,让游子的心愈加宽慰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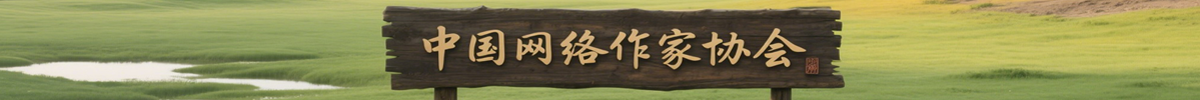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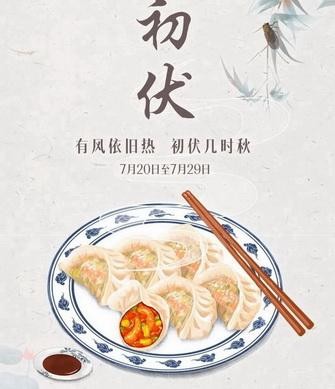








精彩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,请遵守评论服务协议
共0条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