草木有灵 文理相通
〈云雾茶姑〉的生态书写与民族诗学
〈云雾茶姑〉发表中国作家网
文/朱鸿博
拙文《云雾茶姑》蒙方家垂览,诚惶诚恐。此文不过是在黔东南雷公山采风时,拾得几片沾雾的茶青,夹在笔记簿中带回京城的零星记忆,岂敢妄谈创作,惟愿以笔为媒,传递苗家茶事之万一灵光。
一、生态书写的纹理叙事
本文尝试构建一种“草木伦理学”的书写范式。文中对秃杉王树纹与迁徙古歌的互文描写,实则是借苗族“理”的概念,回应西方生态批评中的“地方感”(Sense of Place)理论。阿朵所说的“茶树知道哪片云最疼它”,暗合深生态学“生物区域主义”主张,却以苗家特有的诗性智慧表达——这与美国学者布伊尔提出的“环境想象的物质性”殊途同归,都强调自然客体本身的主体性表达。
二、身体技术的文化转译
文中刻意记载了诸多身体动作:采茶时触碰婴儿囟门般的轻柔、跳舞时裙摆展开的精确半径、银饰随呼吸调节的角度变化。这些看似闲笔的细节,实则是向莫斯“身体技术”理论致敬——苗族的生态智慧不仅存于歌谣传说,更编码在世代传承的身体记忆里。阿朵的舞步实为活态地图。
三、物体系的神圣性建构
从银项圈的弧光到茶汤的琥珀色,苗银饰物不仅是装饰,更是宇宙观的物质载体:项圈上镂空的蝴蝶纹投射在锁骨的光影,这种物性书写,恰似人类学家阿尔君·阿帕杜莱所言“物的社会生命”的文学实践——寻常茶种在京城窗台显现“银球”光泽,正是物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生命轨迹。
四、跨媒介叙事的实验
文末附诗《雷公山恋曲》并非狗尾续貂,而是刻意制造的文本的音乐性。散文部分如茶在水中之舒展,诗歌则是淬取的茶多酚,二者形成本雅明所说的艺术光晕。这种安排既是对苗族舞与歌谣共生传统的模仿,也是对现代散文文体创作的一次尝试。
此文之作,实是怀着对苗族生态智慧的敬畏之心。若能引发读者对民族地区“地方性知识”的些许关注,便是某之大幸。文中必有疏漏之处,尤对苗族文化的理解尚显肤浅,唯望方家不吝斧正,则文学之道,幸甚至哉。
(全文终)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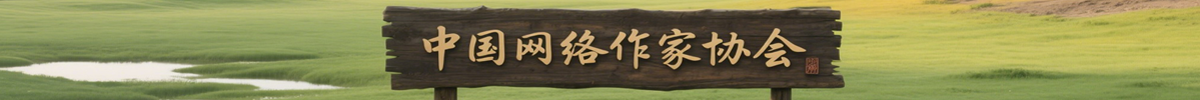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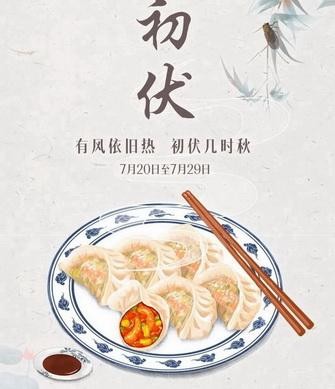








精彩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,请遵守评论服务协议
共0条评论